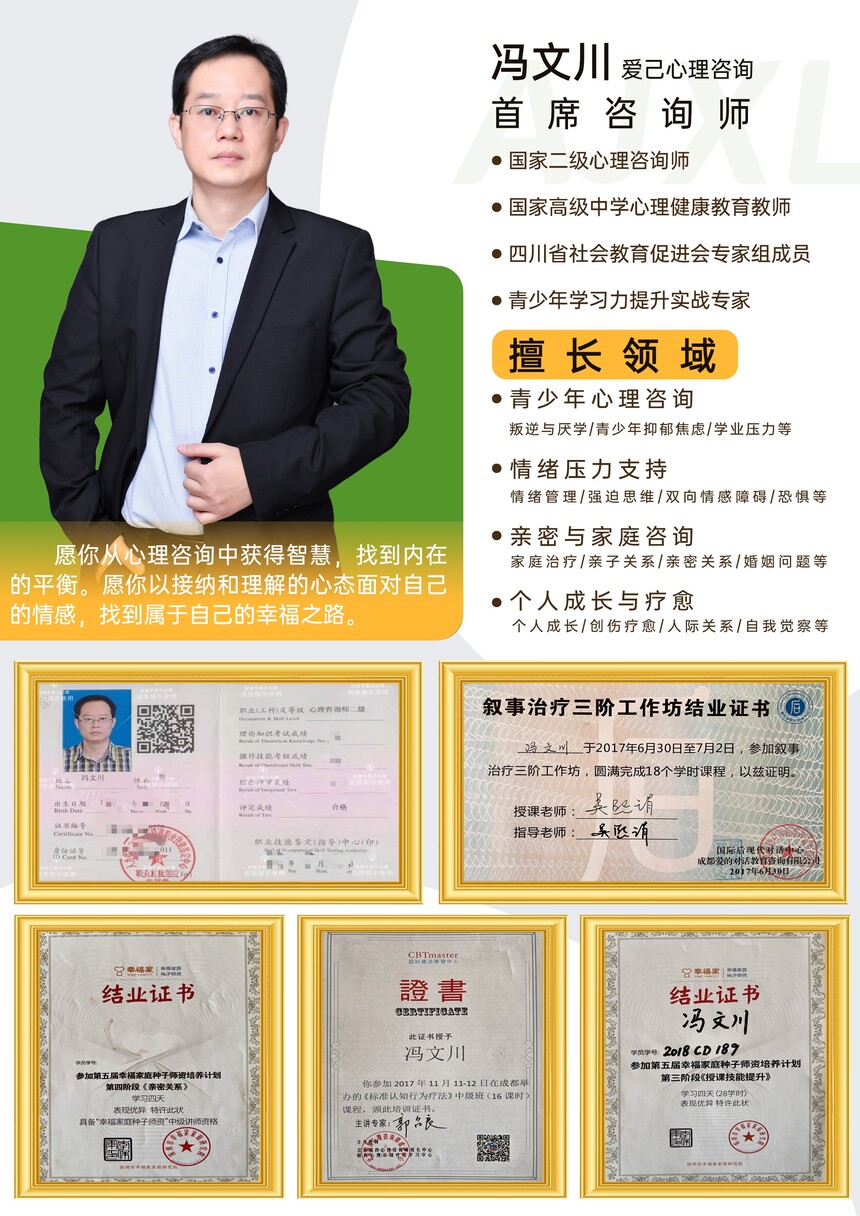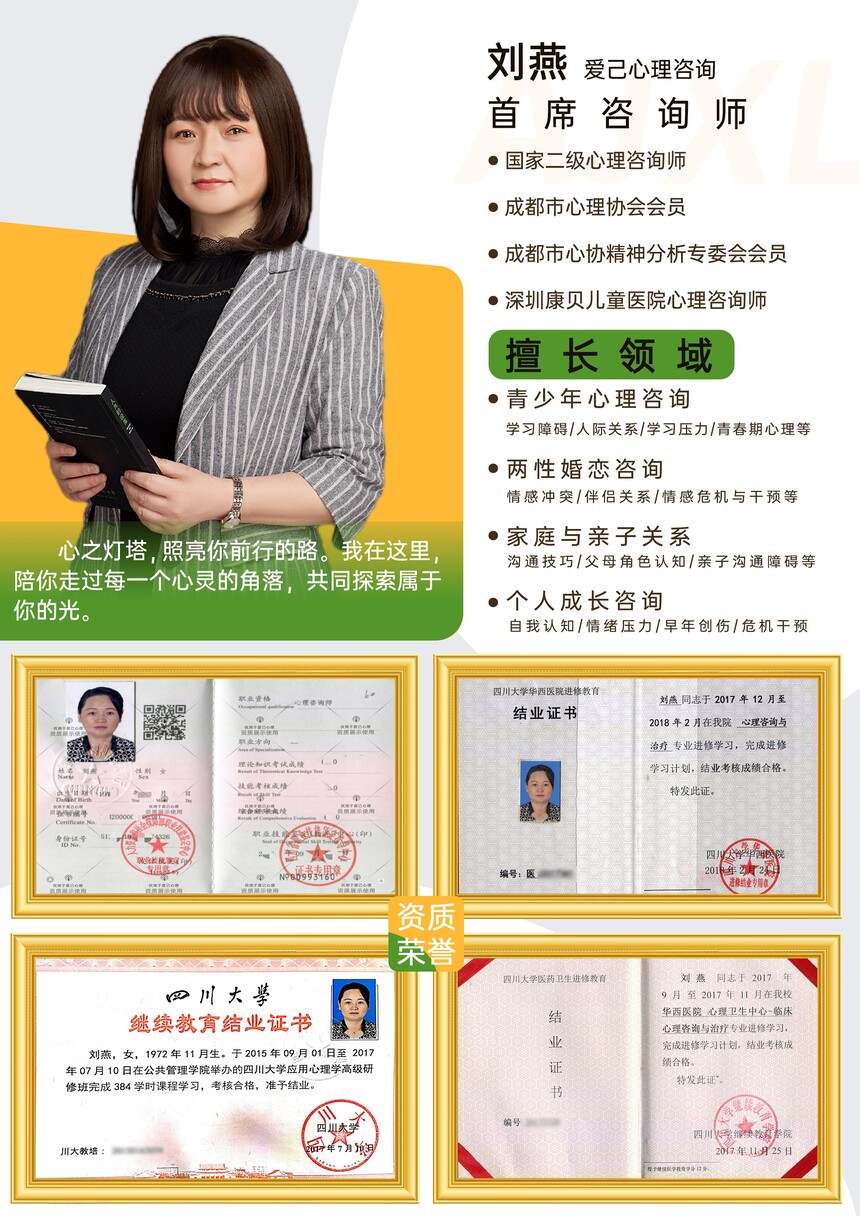|
情感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六年码字生涯:从暗礁到散文诗,心灵深处的神交与滋养时间:2024-11-28 14:06 本文共5153字
预计阅读时间:13 分钟 即使生活充满暗礁,我们也应该把它活成一首凌乱的“散文诗”。 亲爱的读者: 作为一名普通的心理咨询,我在心理公众号上写文章一转眼已经六年多了。加上我随意给纸质心理学期刊投稿的那些年,已经快十年了。已经是年底了。 回望这些年的每一个细节,脑海中时常浮现一条闭环的生物链——“访客——顾问——读者”。 这些年来,咨询师陪伴着来访者,读者也陪伴着咨询师。我们就像来自五湖四海的精神朋友,在心灵深处互相呼应,互相滋养、互相支撑,各自扭折着各自的人生轨迹。 走着走着,一些游客加入了读者的行列。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是对辅导员说:“我希望你能把我的故事变成文字,也许有人和我有相似的经历,也许有人会像我一样。”共鸣,我会觉得茫茫人海中我并不孤单。” 于是,一些参观者成为了辅导员文章和故事中“变身”的主角,自然吸引了一些同情的读者。 随后,有读者或思考良久,或心血来潮走进咨询室。他们对顾问说:“我看到了你的文章,我也希望能得到和文中一样的突破和转变。” 自然,顾问写的故事要丰富得多……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全国各地都流行有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我也未能幸免于此。我非常虔诚地做了这样的梦。我曾经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一句话: ” 生活 拉开一看, 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那就是 青春如诗, 中年就像一本小说, 老年就像散文。 ” 我记不清是从别处抄来的还是自己编的。 总而言之,在我的青春岁月里,我特别渴望将自己的青春活成一首燃烧的诗。我觉得只有这样做,人到中年,自然就能收获一首荡气回肠、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催人奋进的诗篇。一本让人落泪的小说,然后到了老了,才会安心地与爱人携手“看庭前花开花落;看天上云卷云舒” ,然后以泼墨般的自然心境谱写出一首“不遇恩宠不惊,无心离去”的写意散文。 曾经,我坚信,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会像徐志摩的《送别康桥》一样: ” 我悄悄离开, 当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挥手, 告别西天的云彩。 ” 然而,在我彻底走出青春的行列之前,我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梦想是梦想,现实是现实。 我的痴情不会变 我的心永远不变 用“诗意”的角度看待生活 他有点咬牙,安慰着同样为“以文交友”而困惑的知己,也催眠了自己:“即使生活布满礁石,也要像一首凌乱的散文诗一样走过人生。对不,我们为何来到这一生?”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男人的两鬓明显沾满了白发,“独行千里”之后的他依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所以对任何人来说我们都不觉得陌生。 我带他去了我家门前临街的一家小餐馆。他在夕阳笼罩下的玻璃窗前,认真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当年很喜欢你的那句‘生活是一首凌乱的散文诗’。我还是真的一步步活了下来。后来,我听说你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我觉得这个职业很适合你的特点。” 看着对面那张不再年轻的脸,听着他平和的情绪,我突然觉得岁月的沧桑却又温柔,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真的曾经年轻过,而且似乎还没有年轻过。彻底失去了我们的青春。 虽然他没有成为诗人,但我也没有成为作家。 再次重逢,心中依然涌动着诗意的痕迹,有我们过去的青春、迷茫、纯真,也有我们一路走来的严肃、无奈、艰难。 这种诗情是灵动的、自然的、亲切的、温柔的、写意的、水墨风格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芳村咨询室与每一位来访者一起努力,希望把心理咨询打造成这样一幅诗意的画卷。 从访客的反馈来看,有时确实有效,但也有很多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 我努力放下挫败感,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请深呼吸,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慢慢来。” 所谓痴情不会变,心永远在。 也曾有一些学历特别高、学历特别高的年轻同事对我哀嚎:“姐,姐,你怎么不留我啊?我早早就精心准备好了第二次会议的大纲,她却没有”不打招呼。”你们就判了我死刑,却没有告诉我我是怎么死的。你是如何让第二十次来的客人来的? ”
我搂着她的肩膀,对她说:“也许是我自卑,没有你那么系统的理论知识;也许是我太痴情,才子佳人的小说看多了。”当我年轻的时候。” 继续说下去,我不自觉地就失去了乐趣:“也许,当我听他们的故事时,我的心里浮现出的是散文诗。即使它们是杂乱的、痛苦的,我仍然把它们当成散文。诗歌。相反快速旋转“他还处于口语阶段”或“他有边缘性人格障碍吗?”这样的词 所以,亲爱的读者,今天我特别想尝试用一种文学的方式,把在诊室里写的一篇长篇小说解读成一篇写意的散文。我也希望你有散文般的心态。去看看吧。 请和我一起向林格和她的情感障碍致敬。 寒冬里的第一次见面 与灵儿的咨询关系在COVID-19大流行的第三年儿童节前夕被暂停。她特意约了这样一天对我进行最后的闭幕采访。 她说,她想郑重地送给三年级的儿子一份节日礼物——一个温柔、温暖、稳定的母亲。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很感动,对她说道:“这也是你送给当年那个小学三年级的小灵儿的礼物,也是离别的礼物。”你送给我的礼物。” 她眼里泛着晶莹的泪水,用力地点点头。 送她到门口后,她又问道:“如果以后我还想过来的话,可以吗?” 我对她温柔一笑:“当然,我们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一定会遵守诺言的,对吧?” 她轻声道:“谢谢你,再见。” 我回答:“再见,请友善一点。” 她向我伸出双臂,我轻轻地搂住她,拍拍她的肩膀。 她确实离开了,这次我们谁都没有说“下次见”。 我只能看到那个穿着合身淡紫色连衣裙的轻盈身影。 我慢慢地将病例报告按照她的号码按顺序排列在活页纸上,全部编码,装订成册,并在封面上写下开始和结束日期以及咨询的总数。 他的双手一刻不停地移动,脑子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将时间倒回几年前。 如果你此刻正在读这几个字,你的脑海里确实有一个大屏幕,那么请让我告诉你,那个屏幕上慢慢映出的,是几个巨大的黑体字“九年前……”。 粗体文字的背景是萧瑟的冬天。草木枯黄,飞鸟不见踪影。街上的大槐树已经没有留下任何叶子,只剩下形状各异的细枝,向灰暗的天空伸展。 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刺骨的孤独。 那天是2013年元旦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天气预报说有小雪,但直到下午才下雪,天空阴沉沉的。 这天下午,灵儿在刚结婚的丈夫的陪同下来到了诊室,丈夫当年27岁。 我从她丈夫的电话里已经大致了解了她的故事:灵儿不是本地人,她的老家在华南边境的一个小镇,两人是大学同学。他们同学四年,恋爱三年。毕业后,灵儿为了一场爱情,毅然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丈夫一家人深受感动。公公婆婆把她当成女儿,嫂子干脆放弃了“嫂子”的称呼,改称“姐姐”。 结婚后,她尊公婆如亲生父母,爱嫂子如亲妹妹。 幸福的家庭是所有亲朋好友都羡慕的。 但结婚不到半年,婚纱还温热的时候,灵儿就到了三十一层楼顶想要跳下去。幸好跟踪她的丈夫及时接住了她。 当他们第一次在咨询室见面时,夫妻俩得到了医院精神科的诊断——情感障碍II型。 我心里很不安,小心翼翼地问她:“你按时吃药了吗?” 丈夫替她接听:“她在吃饭,我每天看着她吃饭,医生嘱咐我们要做同步心理咨询。” 我犹豫着,心里很犹豫,“这么严重,我能应付吗?” 同时,我的心思也在快速筛选自己熟悉的同事,考虑哪位顾问的风格更能支持她。 也许是敏感的灵儿察觉到了我的犹豫,于是她低声说道:“老师救救我,好难受,真的比死还难受。” 慈悲的“奶奶” 那时的我刚入行几年,正不知疲倦地、着迷地和自己自发形成的个人成长群体中的伙伴们一起分析自己的各种潜意识,无情地梳理自己的所有细节。未完成的感情。
她还坚持留在一个以图像对话为主的自我体验小组。沉深闹说,整天看各种图像,拆自己的副人格,把自己拆成碎片,又跌跌撞撞地重新组装起来,过一段时间又拆。假装,做各种自虐行为。 那时,我清晰地体会到,孩子身上有一位充满慈悲的“老奶奶”。用精神分析学家的话来说,这个“老祖母”可能是从我自己的祖母那里内化而来的。 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奶奶的理解中,她认为一切都应该好好对待,包括特定时代需要国家行动彻底铲除的“四害”。 我清楚地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还把一个学生一个学期交出的老鼠尾巴的数量作为评选“三好学生”的条件之一。 小时候,可能是父母工作忙,也可能是爷爷早逝,父母希望我能陪伴奶奶。不管怎样,我记得在上中学之前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奶奶住在一起。 奶奶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有一个固定的作业,就是在外屋的地上撒一把谷物,有时是一把小麦粒,有时是一把玉米粒,然后听她自言自语关于躲在房间里的人。黑暗角落里的老鼠:“我已经把粮食给你们收起来了,记住别咬我装粮食的麻袋。” 但奶奶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老鼠对她撒在地上的粮食视而不见,反而去咬她装满粮食的麻袋。尽管麻袋被抬离地面,下面有小板凳,但老鼠仍然有能力。跳起来咬一个洞。 于是,奶奶的每个麻袋上都贴满了不同的补丁。除了麻袋本身的自然磨损外,大部分都是那些不听话的老鼠干的。 我记忆中另一个特别清晰的场景是,在我和奶奶住的老房子里,经常有不认识的人来住下。 有时是精神不稳定的中年妇女四处漂泊,有时是守寡的老太太,儿子被认为不孝,没有家人,有时是不能生育、经常被人欺负的年轻儿媳妇。被婆婆家人欺负。 …… 不管怎样,我和奶奶的餐桌上时不时就会有第三个人。 那时信息、物流不发达,但人文气息却很发达。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里,大多数人都互相认识。 每当这些人来投靠奶奶的时候,赶集的时候,村里的人自然会挨家挨户地给各自的家人传话。 随后,他们的一些家人来到奶奶家接他们。有的家人还会带一些自制的零食给奶奶表达谢意,这些零食往往很快就到达了隔壁住户的嘴里。 而且,每当遇到极端的冰雹天气,或者连续几天的阴雨,奶奶都不敢抱怨、咒骂上帝。这时,奶奶总是像一尊雕塑一样盘腿坐在窗前,愁容满面,表情悲切。他自言自语地祈求上帝:“请不要再这样了,如果再这样的话,我真的就拿不回粮食了,我就活不下去了。” 记得成年后,我偶尔和父亲聊天,说起奶奶毫无原则、有些过分的追随。 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只说道:“你奶奶是一个经历了太多苦难,被命运欺负的人。” 既有心痛,也有隐忍,也有无原则的纵容。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奶奶很幸运,有一个像她这样的父亲作为儿子。经常来投靠奶奶的寡妇老太太,曾无数次向奶奶表达过这一点。无尽的羡慕。 在我非常迷恋《红楼梦》的那些日子里,我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我的奶奶与刘奶奶进行比较。 他们也经历过艰辛和贫穷,但刘奶奶在卑微的外表下却有着内心的开朗和坚忍,而我的奶奶几乎总是对人对事温柔顺从、逆来顺受。 我是在这样的奶奶的陪伴下长大的,自然受到的启蒙教育就是,虽然简单,却因大量的恐吓而带有浓浓的迷信味道,“人在做,天在看”、“有是高过头三尺的神。” 可想而知,无论我的潜意识里有多少人性的邪恶,我都绝对不敢表现出来,因为我总感觉有一双碧绿的眼睛在我头顶三尺处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不敢做出任何举动。任何错误。 因此,我小时候就走的是“懂事、乖巧、别人家的孩子”的路。我得到了很多赞美,享受了很多特权,压抑了很多本性,限制了很多个性发展。 这一切在进入心理学领域后被血淋淋地揭露出来,将自己两三代人的人生翻了个底朝天,对自己进行了各种非人的分析。 难怪我的副人格里有这样慈悲的“奶奶”形象。 十年旅程开始 当她第一次见到灵儿时,她低声说道:“老师,救救我吧。”然后她把这个“奶奶”叫到了对面的椅子上。 我毫不犹豫地给了灵儿最温暖、最温柔、最坚定的眼神,回应她:“好,我和你一起努力走完这条泥泞的路。” 当我们的咨询关系走得很深的时候,灵儿曾经告诉我,她说:“老师,当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我就感觉被您的目光锁定了,所以我愿意听您的。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先告诉你吧。” 我记得当我和她签署咨询协议时,我几乎是半是哀求半是威胁地央求她:“既然你来找我了,当你想结束生命的时候,请记住,我有知情权。你一定要先跟我打个招呼,再跟我商量一下,你是个善良的人,不能让我失去留在这个行业的勇气。” 我承认我有点道德绑匪,但对于当时如此害怕的我来说,我能做什么呢? 而当我听到灵儿告诉我她遵守协商协议的真正原因时,我还是有些羞愧,感觉自己像个小人。 就这样,2013年冬日一个阴沉沉的午后,一位出于热忱而半途出家的年轻心理咨询与一位处于抑郁期、急需就医的情感障碍患者结成了伙伴关系。对于“生死相依的伴侣”,准备跨越未知的泥潭。 但我们谁也没想到,我们开启了近十年的旅程,而那年冬天我们签下的,竟然是一份漫长的合同。 。 。 待续... 过去推荐的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