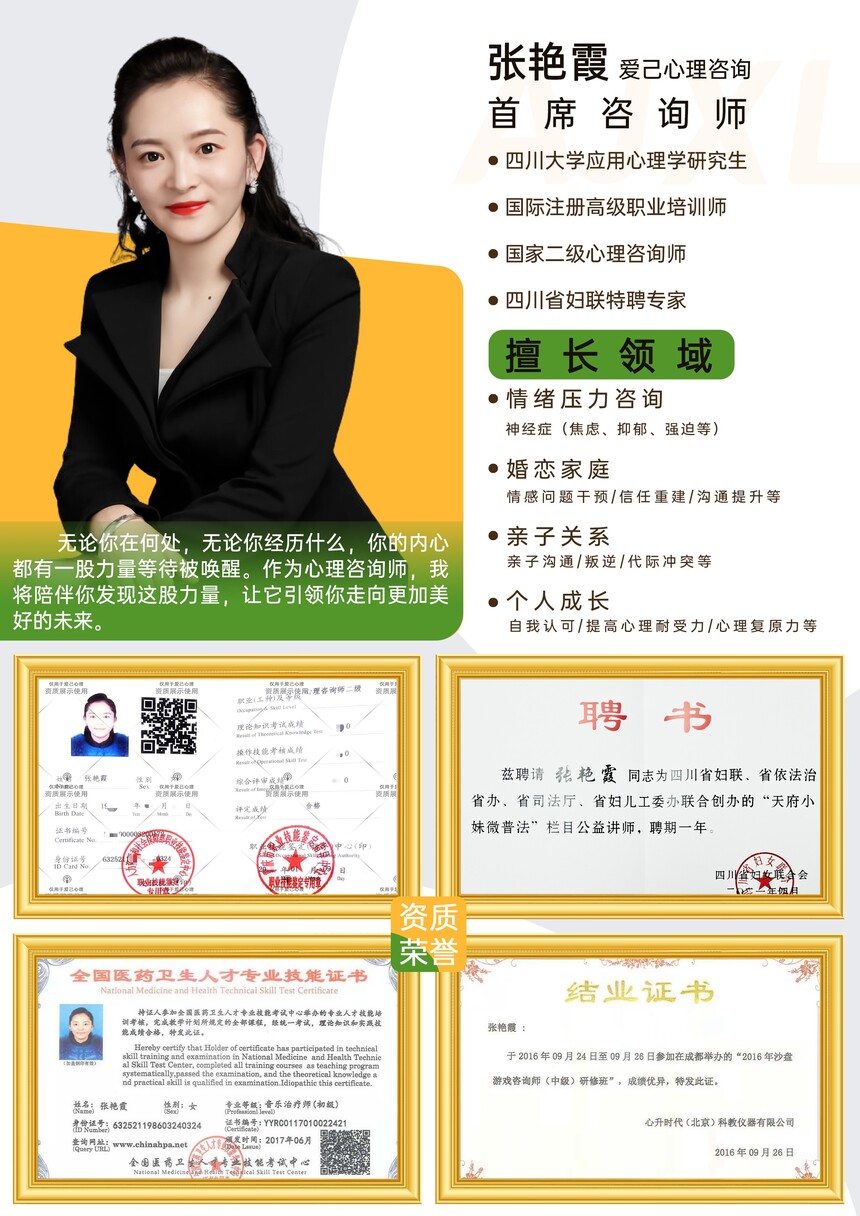|
去哪找心理医生疏导|上海疫情封锁期间女性心理危机与医疗求助困境的真实故事时间:2024-12-16 14:08 澎湃新闻记者 朱颖 实习生 丁朝义 薛克贤 孟军 李明志 电话一接通,女子就开始哭,语无伦次。 心理咨询咨询师苏红没有说话,只是听着。 哭了20分钟后,女子才稍稍平静下来。苏洪这才开始询问她的情况。该女子称,她一个人在上海打工,丈夫和孩子都在老家。上海疫情爆发后,她独自在家。她的胸部突然出现了三道伤口,不断渗出脓液。她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疱疹。伤口感染了,没有药。 她给上海的社区和各大医院打电话,都说要等疫情结束后才能做手术。 “我感觉很糟糕,没有人能帮助我。”她每天都想跳楼。有一天,我去居委会填资料时,偷偷带了一把刀。 电话那头,苏红告诉她,她的新冠肺炎患者生命支持慈善团队有专业医生可以帮助她。 打通电话后,苏红成立了关怀小组。医生在群里给予指导。她可以用生理盐水冲洗该区域,然后使用皮肤抗菌液。其他志愿者帮忙联系医院,发现她的病情只能在疫情结束后到龙华医院治疗。进行手术。 当天下午,女子发来一条信息:“虽然我们都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粒尘埃,但你们这些普通人仍然面朝太阳,努力拯救每一个濒临崩溃的生命,真是了不起。” ” “我会挺过去的,”她说。 这两个月来,苏红收到的这样的求助实在是太多了。她所在的NCP生命支持队曾为受武汉疫情、西安疫情、吉林疫情影响的人们提供心理援助。 3月31日,上海疫情援助启动。 此前,上海心理热线、上海抗疫心理关怀热线等心理援助热线已开通。 在封城和沉默的两个月里,疫情引发的各种情绪,夹杂着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萦绕在上海人的心里,随着城市的重启而慢慢消失。 女子给苏红发了一条消息。 “每一次拨打热线电话都是一次生命” 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3月中旬开始,连通注意到与疫情相关的电话增多了。 莲桐是上海心理热线“”的接线员。该热线24小时在线,有300多名心理咨询。 4月初的高峰期,每天有超过400个电话涌入。 平时全国各地都有,但从3月份开始,几乎全部来自上海。有的群众拨打“12345”、“120”打不通,转而拨打心理热线。 连彤发现,电话中不仅有因封锁和隔离而引发的情绪问题,还有一些患有急性焦虑和抑郁的患者,长期封锁后病情恶化。此外,还有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比如企业裁员、资金链断裂等;以及隔离期间加剧的亲子矛盾。很多来电反映的并不是心理问题,而是现实问题:缺药品、缺物资、未能转运住在一起的阳性患者。 联通会告知求诊者相应的就医、配药热线及渠道。如果情况紧急,建议拨打“110”或“120”。如果是曾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的患者,他们的信息将被记录并反馈给医院。 2022年4月19日,上海,长宁区一条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夜晚依然灯火通明,众多社区志愿者为封闭区域的居民提供配药服务。人们的愿景 上海抗疫心理关怀热线负责人秦海也有类似的发现——拨打热线电话最初都是出于实际问题。 为此,志愿者收集整理了各种配药流程、紧急电话、团购渠道、公益组织联系方式等信息,提供给求助者。我们还帮助寻求帮助的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发送求助信息,希望信息传播出去后,有人能够联系到他们。 “每一次拨打热线电话都是一次生命。”秦海觉得自己能帮忙的一点点都是值得的。
马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中国首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团队成员。 “(这)称为社会支持。”马洪表示,灾难发生时,最重要的是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问题。武汉疫情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戴口罩能行吗?超市关门了,社区关门了,没饭吃可以吗?不行。没有社会支持,我派一群心理医生也没用。喝水,找人,搞情报,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说他还着急吗?” 上海福嘉文化的危机干预心理学家尹晨芳也有同样的感受。疫情期间,她被困在上海家中,购买物资极其困难。 “有的人已经饿了四五天了,每天都喝白开水。这个时候,如果你告诉他们,‘哦,你要冷静’,那是没有用的。只有确定什么时候能拿到食物,或者能拿到食物,我们才能安定下来。” 为此,她当上了小组长,联系供应商、供应保障单位,帮助社区居民整理蔬菜。有时她凌晨四五点就起床去取货。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让每个人都买食物。”尹晨芳说,当人们看到希望时,心态自然会好转。 2022年5月25日,上海杨浦区一小区门口,几名青年志愿者和“领队”正在对居民分组购买的整箱西瓜等生活用品进行分类、包装和发放。人们的愿景 连通表示,经营者只能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帮助一些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热线电话一般不会超过30分钟,“这相当于快餐服务”。 有很多实际困难是他们无法解决的。 一位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女老板看到上海心理热线广告上的“我陪你度过难关”的标语后,拨打了上海心理热线。接线员王怡然接听了电话。 女老板说,她不喜欢“忍耐”这个词,但她实在是没办法——她的公司受疫情影响,资金链断裂,员工工资发难。说着说着,他就开始哭了。 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的妻子和孙女都被感染,住在不同的避难所。老人打电话问,我老婆可以转到我孙女的小屋吗?我可以去收容所照顾我的孙女吗? “我不怕感染,只要孩子心情好一点,我就没有问题。”老者说道。 王怡然说,在这些时刻,接线员能做的就是倾听、换位思考,给予一些安慰和鼓励,让他们放心,疫情不会持续太久,会好起来的。 让情绪表达 在家坐月子的日子里,心理教练庄文杰常常感到愤怒和无力。 她发现身边的人都忙着抢菜,社区团购群里争吵不断,与疫情无关的工作群、校友群也弥漫着火药味……整个城市的状况已经严重恶化。” 暴露在疫情的环境噪音中,庄文杰意识到个体很难独处。一方面,人们的安全感、满足感、联系感受到影响。他们不知道自己会被关押多久,压力很大;一方面,人们更能够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产生更强烈的同理心,比如一些不公正和一些不可接受的行为。 “我会觉得不对劲,但又无能为力。”庄文杰说。 苏洪的感触更深。从4月1日到5月15日,她的NCP团队护理小组收到了312条心理帮助信息。 “其中很多是疫情带来的痛苦经历导致的暂时性身心障碍和情绪变化,比如焦虑、崩溃,甚至自杀、自残。”苏红解释说,在疫情的持续刺激下,有些人会出现流行病综合症——全身酸痛、睡眠不好、做恶梦或食欲不振;情绪烦躁、悲伤、抑郁;生活不规律,不爱说话,不愿意与人接触,甚至有报复行为。 苏红说,在这种压力状态下,人们会选择“战斗还是逃跑”——要么战斗,比如当小组长、志愿者等;要么战斗,比如当一名志愿者。要么就逃跑,在家躺着,什么事也做不了。 苏红曾参与武汉疫情期间的心理危机干预。她发现,在上海,人们面临死亡并不是因为害怕感染,更多的是因为物资和医疗药物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者长期处于封锁状态,看不到希望,从而导致情绪低落。变化。 这时,心理热线的作用更多的是陪伴。 “很多人一接电话就会觉得有人还在关注自己。” 苏红接到一名男子的求助。 另一人30多岁,两岁半的孩子核酸异常。发烧退后,自检抗原检测结果呈阴性,他不得不被转移到避难所。他担心孩子太小,与父母分开后得不到照顾。他还担心庇护所的条件。他不想被调动,希望社区来找他进行核酸复检。但根据规定,红码人员只能到机舱进行审核。 在社区里,如果有人攻击他们,如果他们不走开,其他人就会被感染。他和他的妻子都有些沮丧。 收到求救信息后,苏红拨打了电话,但该男子一开始拒绝了。苏红教他深呼吸,进行渐进式肌肉放松。 男人开始说起了家里的情况。说着说着,我就泪流满面。
哭了五六分钟后,他说:“很抱歉让你笑了。” 苏红安慰他,每个经历过同样事件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你不必压抑自己的情绪,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有的求助者会问苏红:“你看到我的笑话了吗?” 苏洪说道:“我很担心,你能问我这个问题,说明你信任我。” 她发现,说完这句话后,求道者往往愿意交流。 “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不正常,但实际上很正常。” 苏红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未表达出来的情绪永远不会消失……总有一天它们会以更丑陋的方式爆发出来。” 庄文杰也认为,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发帖、运动、健身操、和别人聊天都是很好的释放方式。 “先有情绪,后有问题。”苏红遇到过很多寻求帮助的人,她表示自己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此时此刻,心理咨询要做的就是成为求助者的助手,帮助他“稳定情绪、保证安全、提供支持”。 具体来说,根据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心理急救指南中的“看、听、寻求”原则——从服务对象的声音和描述中“看到”他的真实想法,并用心倾听和“倾听”,然后引导寻求者找到解决办法,帮他梳理流程,告诉他如何与外界联系。 但在某些情况下,“逃避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尹晨芳说。 “我不会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只是等通知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只要能吃好喝好,保护好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就可以了。” 对于如何调节情绪,尹晨芳的方法是:告诉求助者一些比他更“惨”、更不容易的事情,让他知道自己不是个例,然后引导他看到好的一面。他自己的各个方面。 ,提升自我价值。 秦海建议大家多和亲戚、朋友、同事保持联系。 “不要切断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虽然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但岛下有海水将我们紧密相连。” 那通电话的时候,那人哭了之后,苏红就拉着他深呼吸调整一下,然后一起商量转接的方法。聊了一个多小时后,男子表示感觉轻松了很多。 苏红还帮他联系了保山方舱医院。随后,男子接受了社区的安排,一家三口来到了收容所。 危机干预:“我们必须给她希望” 4月16日,苏红收到另一位心理咨询的求助。 这是一名30多岁的女性,患有精神分裂症。平时吃的奥氮平片和氨磺必利都没有了,她想去医院拿。小区被封锁了,她出不去。 两天前,她半夜起床,与合租人发生肢体冲突。以前她生病的时候,曾用刀伤过人。这一次,她怕自己生病了,半夜砍人怎么办?我急得睡不着,想自杀。 苏红迅速对她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危机是指超出人们应对能力极限的风险,可能导致崩溃、自杀、自残等。 苏红介绍,当人们遇到重大事件或精神压力造成的暂时性身心障碍时,第一阶段是心理急救和危机干预。越早干预,就越能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最好的时间是48小时,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在一个月内。 2008年汶川地震后,心理危机干预在国内开始成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办公室主任钱英表示,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发生火灾后,国家第一时间派出心理专家前往救援。这是中国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开始。 “疫情推动了心理危机干预的普及。”钱颖表示,危机干预培训以前比较小众。疫情发生后的近两年,受到政府和媒体的关注,各省市都成立了专业团队。 在危机状态下,求助者常说,“我感觉很不舒服,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死,我该怎么办……”苏红回忆,危机干预就是在人们感到窒息、黑暗时提供帮助。心灵“做一次心肺复苏”,重新获得生活的掌控感和自信。 收到求助后,苏红建了一个群,邀请心理医生一起讨论情况。她向“110”、患者居委会以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沟通了情况。 “110”民警带走了患者的身份证。请携带好证明、处方、病历卡,到精神卫生中心找医生开药。 拿到药后,患者情绪稳定下来。 苏红说,由于封锁时间较长,“太多人有自杀倾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患有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年轻人。 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心理干预。苏红遇到一名停药后病情复发的躁狂症患者,威胁她的父母,“如果你去(医院),我就自杀。”苏红为她提供心理疏导,但她不愿意。 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尹晨芳在网上做了危机干预。起初,女孩也拒绝了。 当时正是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女孩和她的父母被锁在家里。这个女孩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她的父亲死于 COVID-19,好几天都没有人来接走尸体。她的母亲呼吸困难,无法入院。女孩在微博上寻求帮助,但没有人能帮助她。 当殷辰芳给女孩打电话时,女孩绝望地说,如果她妈妈死了,她也活不了了。 她拒绝心理干预,称自己不需要心理干预,只是希望有人把父亲的遗体运走,给母亲一个氧气瓶。 “我们必须给她希望,而且是巨大的希望。”尹晨芳告诉团队志愿者,一定要让女孩看到,他们有能力帮她解决问题。 随后,一名志愿者找到人脉,帮女孩拿到了氧气瓶。 尹晨芳表示,人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核心原因是支持系统出现问题,比如家庭或者父母的问题。危机干预最重要的是帮助寻求者找到支持体系和资源。 5月中旬,尹晨芳接到街道妇联的电话,请她为一名精神失常的女孩提供帮助。 那个女孩当时正在读大学三年级。她原本精神良好,核酸呈阴性。但因为有人约她去收容所,她的情绪崩溃了。她拒绝吃或喝。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想要跳楼。听到外面喊“核酸”,她就疯了,不让父母下去做;她不接电话,她的父母也不准接电话。父母都吓坏了。 尹晨芳通过微信指导女孩妈妈在家少说话,减少言语刺激,不要说孩子的坏话,并要求社区人员不要在她家楼下喊“核酸”或强迫她做核酸。每隔两三个小时,尹晨芳就会询问女孩的情况,并给她母亲一些注意事项。 过了两三天,女孩的情绪逐渐稳定,不再摔东西,愿意开门,也愿意吃药、吃饭。 需要关注人群:医疗、青少年、独居老人 “你知道吗?现在对我们来说太困难了,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女孩在电话里情绪非常激动。 她是上海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自三月初以来,她一直被困在医院。她每天清晨乘车前往偏远的老城镇和乡村,然后步行到居民家中采集核酸。有时找不到路,居民就会问,你怎么迟到了? 她的男朋友是一名医务人员。好久不见,父母也照顾不了她……护士支支吾吾地哭着说她想回家,“什么时候解封?” 3月底,秦海不知道如何回答热线那头提出的问题。作为专门的医疗热线,琴海上海抗疫心理护理热线接到的电话 %来自医护人员。 长时间高强度工作、身心疲惫、随时可能被感染、疫情何时结束的不确定……是一线医护人员的共同感受。 但他们很少表达这些感受和情绪。秦海发现,医生和护士可能感觉自己无法多次得到照顾和支持,所以拨打热线求助的人相对较少,而拨打热线求助的人很多都已经处于崩溃状态。 后来,秦海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愿望,那就是让护士在大白纸上写下“我想回家”。 两三天后,护士去看望她时,说她好多了。后来她在大白纸上写下了“上海加油”,因为只有上海好起来了,她才能回家。 一些医护人员本身也被感染。秦海说,有些医生和护士会感到内疚和自责,因为如果自己摔倒了,其他同事就会更忙;有的甚至不好意思自省,不知道是哪个环节造成了问题。 秦海接到了医生的求助。他说,自己正忙于防疫,妻子也是一名医务人员。感染后,她感到非常难受和无助,不再接听家人的电话。他非常担心,希望志愿者能够帮助妻子平静下来。 当秦海打电话时,发现妻子正在船舱里,和其他医生护士一起照顾病人。她说,她的愿望是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有一个单独的病房,这样他们就能尽快康复,继续工作。 秦海将建议转发给上海医学会后,很快得到落实。 4月中旬,秦海团队对医护人员进行了心理状态评估,发现部分医护人员出现严重焦虑、严重抑郁症状。 钱颖曾在武汉疫情和西安疫情期间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干预。让她惊讶的是,不少医生和护士表示,他们很难过要抢救病人,又没有呼吸机,只能给他一个氧气瓶。 “他觉得作为一名医生他救不了人,这让他崩溃了。” 除了医疗护理之外,几位辅导员还收到了许多青少年的帮助请求。在家上网课、与同龄人分离以及与父母的关系紧张,导致一些青少年出现焦虑、抑郁甚至自杀。
苏红收到一位父亲的求助。他的儿子在一所重点中学的班级里排名前五。疫情期间,他用手机上网课,然后沉迷于玩手机游戏。他不想去上课,无论他如何努力与父母沟通,也没有用。 王怡然接到了一个初中男生的电话。他是班长,成绩很好。疫情期间,父亲在外地出差,无法回来。他的母亲是一名志愿者。他觉得自己每天在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心里很难过。我每天都要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学?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是独居老人。苏红发现,老人打电话求助时,更多地提到医疗、食物或物质问题。很少有人表示他们感到不舒服并想通过电话交谈。 一些老年人在经历了疫情后会产生怀疑甚至偏执。她接触到一位老人,老人感觉有些不适,她说:“哦,我一定是被感染了。” 还有一些老人独居,孤立在家中,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感到绝望无助,严重时有自残或自杀的念头。 苏红表示,疫情结束后,他们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人群。 心理咨询咨询师,走进疫情 这个五月,是尹晨芳最动荡的一天。 我儿子的核酸数据没有上传,混合管发现异常。经审查,他被拉至机舱,四项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没想到,他从医院回家时,车上人太多了。回家后第二天就出现症状,被感染。 ,又被拉回了船舱。儿子咳嗽了一整夜,尹晨芳感到绝望。 她身边的很多亲戚都被感染了,包括患有严重肾炎的母亲,还有疫情期间心脏病发作的父亲,这让她一直心存忧虑。 “这都是心理创伤。”尹晨芳表示,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无法一下子想通”,只能慢慢调整。 同样感到无能为力的庄文杰决心发起危机干预公益项目,为疫情一线人员提供心理帮助——这也是她释放情绪的方式。 起初,她有点犹豫。这样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吗?人的基本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何谈心理问题? 但她还是决定这么做。她觉得,作为一名专业心理学家,还是要“融入其中”,凭自己的经验做一些事情。随后,她和19位心理教练对107名客户进行了心理干预。 营会结束的那天是5月4日青年节。项目发起人朗读了鲁迅的一首诗:“从此不再有火把,我是唯一的光。”庄文杰觉得,这是疫情期间很多做咨询者的感悟。 秦海在担任顾问时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你不会觉得自己完全无助、无能为力,你还是有一些价值的,如果你做了一件事,你还是有用的。”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他也看到了求助者身上的坚韧和滋养。 “虽然他们在寻求帮助,但他们也在积极应对并努力生存。他的生存欲望非常重要。 ” 不少咨询师提到,随着危机干预在国内的普及,心理咨询的专业水平需要进一步关注。钱英表示,辅导员在做心理干预之前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否则很容易因案件而再次受到创伤。 在培训辅导员时,秦海会提醒他们,“我们是临时热线,不要过多介入,我们要照顾好自己。”参与是过度同理心寻求者的情况。当辅导员无法帮助求助者时,辅导员会感到无助;如果他深陷其中,他就更无法帮助求道者——形成恶性循环。 为了避免顾问情感介入,秦海团队的热线电话被设置为每班仅接听三个小时的电话。 秦海提到,2008年,一些心理咨询前往汶川进行危机干预时,来到灾难现场,受到刺激,感受到灾难带来的无助和悲伤。直接被碾碎,立刻被送了回去。 上海疫情期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4月初,秦海团队的一名顾问接到索要食物的电话后感到很无奈。接完电话,我在小区楼下走了近10圈。 那天,他们对辅导员进行了监督,并告诉他,心理咨询虽然不能为寻求者提供食物,但可以引导他通过自助的方式解决问题。 苏红还提到,辅导员不能以救世主心态做自己做不到的事,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 在培训辅导员时,苏红会提醒他们树立心理界限。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有我的使命,我会尽力帮助你,但当我帮不上忙的时候,我要知道如何对你说不。” 她发现一些志愿辅导员无法帮助客户解决他们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养成自我否定的习惯,从而产生压力。甚至有人说我不行了,中途离开了。 为此,NCP护理团队每周召开清心解忧会,为心理咨询和其他志愿者提供沟通和发泄的场所。还有树洞、暖心客厅等为他们提供在线心理咨询。 解封后心理需求开始爆发 庄文杰记得,封城期间,很多人开玩笑说:“现在上海人最怀念什么声音?就是进门的铃声,代表人流。” 6月1日,上海全面开放复工复产,人们再次涌入上海街头。 2022年6月7日,上海,市民在遛狗。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摄 不少心理咨询认为,后疫情时代,真实的心理需求将开始爆发。 苏红说,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震惊、过渡、适应的过程,都会出现心理不适:一是恐惧、不安,有的不敢出门,不敢去公共场所,出门时担心是否会受到影响。要乘坐出租车,乘地铁或去公共场所。驾驶可能是一个令人担忧和敏感的过程;有些人会反复洗手。 第二种是愤怒和易怒。在流行病变化的压力下,人们变得更加敏感。即使是小物质,例如排队进行核酸测试,也可能引起烦躁,脾气甚至冲突。 第三种是抑郁和悲伤。您已经被锁在家里了很长时间。锁定突然抬起后,您出去工作,恢复了原始的生活。您可能会感到疲倦,无法集中精力。 顾问对如何调整和恢复提出了一些建议 - 首先,您需要调整身心状态,让自己慢慢进入原始的工作节奏,并从工作内容进行一些调整以进行工作和休息时间。休息时,您可以进行腹部呼吸,闭上眼睛,放松或听音乐。 重新连接,一个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与亲戚和朋友也有人际关系,例如预约吃饭和一起喝一杯咖啡;还有一个整体联系,包括心态和信念,例如通常喜欢阅读的人。 ,尝试恢复阅读的习惯,那些喜欢体育锻炼的人应该返回进行体育锻炼。 当您觉得有问题时,您可以寻求专业支持和帮助。 秦海建议,在流行病之后,我们应该专注于对患有基本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的医务人员进行干预和心理筛查。 此外,我们应该向医务人员传播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以便他们在发现问题或感到不舒服时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 此外,可以进行一些团体辅导活动,以使医务人员能够在与流行病的压力下平稳过渡到恢复工作和生产。 对于其他人来说,流行病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Su Hong收到了一对父母的帮助。在流行病期间,他们的生病女儿独自生活在上海的一所租房房屋中,并正在准备重新检查。出乎意料的是,她突然生病并在被救出之前死亡。 父母不在城里,不能来上海,所以女孩的尸体只能暂时存放在医院地下室。父母很痛苦,无法接受。 “失去亲人后,这种悲伤的咨询可能会持续10或20年。”苏洪说。有些人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如果您在灾难发生1-3个月仍然有这种症状,则需要悲伤的咨询。专业人士将与人建立不断的支持关系,以帮助他经历悲伤的过程并增强他过上新生活的能力。 三个月后,如果您仍然有症状,则需要创伤护理,专业人员可以在这里诊断,评估和康复,缓解症状,最重要的是,预防自杀。 在武汉流行期间,自Ying曾经指导社会工作者进行心理干预。 他是一个年轻人。他的母亲在流行病前一年去世,父亲死于19岁。他无法入睡,所以他打电话给心理热线,说他一个人,一直看见鬼魂和亡灵,这使他感到非常恐慌。 Qian Ying引导他找到陪伴他的东西。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洋娃娃,每天都抱着它。 Qian Ying还向他发送了医院心理学家记录的指导记录,以便当他害怕帮助他稳定自己的心情并“与恐惧中孤立”时,他可以听听。 后来,他在测试核酸阳性后住院。住院半个月后,他在持续干预后逐渐改善。从医院回家后,他翻新了房子,然后重新上班。 这使得Ying感到许多人在面临危机时可以适应和调整。心理干预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信任大多数人,我们必须相信他们具有自己的韧性。”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