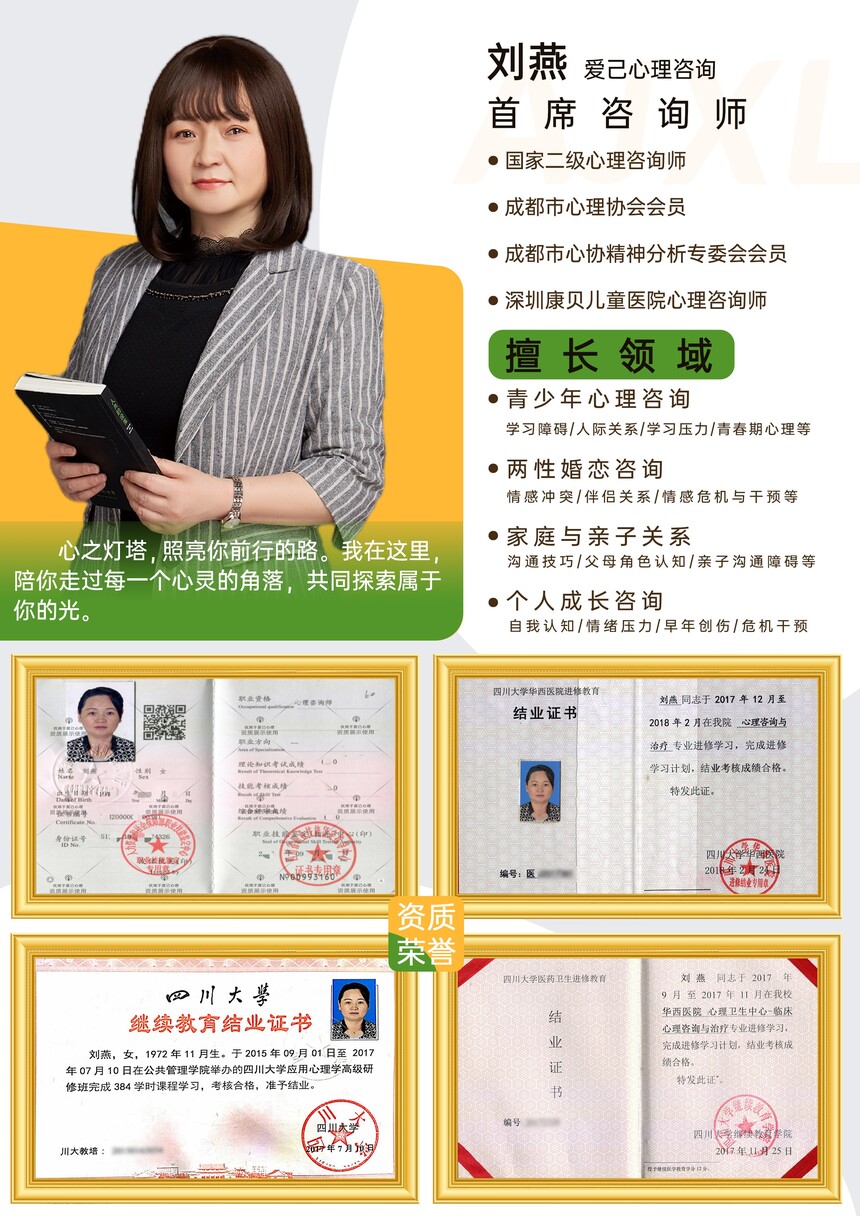|
心理疏导|疫情下的心理危机:心理咨询师朱琳分享如何应对情绪决堤与心理创伤修复时间:2025-01-11 14:08 “我很崩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月29日,心理咨询咨询师朱琳接到求助请求。辅导员一开口,她的情绪就爆发了。 随着COVID-19疫情的持续,公众的心理问题日益成为一个明确的命题。 1月27日,国家卫健委印发疫情期间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要求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总体部署。随后,北京、浙江等地开通了24小时疫情心理援助热线,北师大、北大等多所高校也开通了疫情心理援助热线。 在心理咨询的特殊时期,心理咨询只能通过屏幕通过文字来同情寻求帮助的人。与身体创伤相比,心理创伤需要随着环境和心态的变化慢慢修复。 “疫情过后,更多的人需要心理干预和修复,心理咨询任重而道远。”朱琳说。 突然失衡 “世间一切都难以预料,需要调整心态。” 2月4日,在持续10多天的心理战中,朱琳叹了口气。 与普通心理咨询不同,2014年开始在东莞执业的心理咨询钟建明告诉记者,这次疫情属于紧急情况。当当事人处于紧急状态时,原有的心理状态被打破,正常生活受到干扰,人进入紧急状态。一种“不平衡状态”。 在大庆油田总医院做心理咨询的于雷第一次打电话给杨力(化名)时就哭了。杨丽的父母均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父亲病情严重住院,母亲身体虚弱在门诊静脉滴注。 往返于两家医院照顾父母,对杨丽来说是身心上的挑战。她感到很疲惫,担心自己身体虚弱,免疫力下降,感染病毒,然后传染给丈夫和孩子。
由于睡眠和饮食困难,又无法寻求帮助,杨丽想到了心理干预。在网上寻求帮助后,于蕾接手了她的咨询和帮助。 从事心理咨询6年的朱琳也收到了类似的求助。探索者的父亲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他和母亲一直照顾父亲,但父亲还是去世了。 “请求者的父亲去世了,他和母亲出现了发烧、咳嗽等症状,咳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对他们来说,病床是最好的逃离方式。” 疫情期间心理咨询具有较强的危机干预意识。 “这种流行病的迅速性、传染性和严重性本身对公众来说就是一场危机。内心恐慌和不健康心理状态的身体表现是明显且普遍的。许多人需要心理干预和咨询。 “。”在大庆工作的于蕾告诉记者。 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人群分为四个级别。第一层次是确诊患者和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第二级是居家隔离的轻症患者和到医院的发热患者;第三层次是第四层次,是指与第一、第二层次群体相关的人,如家人、朋友、志愿者等;第四层次是指与疫区相关人员、易感人群以及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的广大群众。 随着疫情的发展,心理危机干预从确诊患者开始逐渐普及到更多人群。 焦虑被隔离 疫情发生后,朱琳成立了一支600人的志愿者咨询小组,主要通过网络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帮助。 由于团队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且有60名咨询师旅居国外,团队接到的求助电话也来自受疫情影响的各个群体,包括确诊住院患者、居家隔离的轻症患者、家属等。住在家里的人。普通隔离人群是其心理服务的主要服务对象。 朱林团队接待的许多客户都患有忧郁症。居住在武汉的一位单身人士在大年初一就感觉眼睛、鼻子很痒。大年初二,他感觉有点鼻塞、流鼻涕,还伴有喉咙痛、头痛。虽然我每天都量体温,也很正常,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符合新型肺炎的情况。
1月20日曾到过武汉的肖波(化名)回国后开始居家隔离。 “从武汉回来后的几天里,我出现了咽炎症状,喉咙发痒就会引发刺激性咳嗽。我去医院检查并做了血液检查。这很正常。医生说我的身体反应因心理影响而加剧。” 北京师范大学疫情心理支持热线负责人林柴华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热线开通至今接到的心理咨询中,普通民众占比最多,约占50%;一线医护人员约占10%,隔离人员约占15%,居家隔离人员约占5%,其他情况约占20%。 战线正在拉长。距离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已有十多天,武汉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在加大防控力度。隔离期间焦虑和不安会加剧。 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热线的心理咨询钟恒接到了一位老人的求助。她居住的养老院已采取隔离措施,缺乏家人陪伴。此外,获取信息的唯一途径是电视和报纸。她了解到的相关信息有限,而且非常可怕。 “也有普通市民呆在家里,由于多日在家缺乏锻炼,消化能力和食欲都不好,也感觉身体缺乏活力。虽然理智上知道不要惊慌,但他们无法‘不由得产生怀疑,反复测量自己的体温,焦虑。”朱琳说。 2月3日,武汉一家企业联系朱琳,希望为400多名员工提供集体咨询。 “有的同事精神不稳定,白天不敢出门,晚上焦虑失眠。” 求助者提到,在疫情较严重的武汉地区,精神状态普遍很差。当我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时,我感到害怕。小门被封住,不许出入。门口站着警察和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我感到害怕。 “公众看到这种情况,难免会有反应。”朱琳说。 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同理心 “首先是倾听,有时候仅仅倾听就能给对方很大的支持。”接受采访的心理咨询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于雷曾参与黑龙江公交车群体伤害事件的心理干预。当时,她和她的团队完成了对伤者及其家属的危机干预。 “在危机干预中,集中倾听和适当的同理心是最有效的心理咨询方法,无需花哨的技巧。” 当听到电话那头杨丽哭诉的故事时,于蕾的心七上八下。她感受到对方的焦虑、无助和绝望,寻找心理咨询的途径。 “我注意到来访者父亲的信息,他已经70多岁了,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这次感染比较严重,年龄和身体状况都不占优势。”玉蕾说道,杨丽却提到了一句话,“父亲很乐观。” 心理咨询的切入点找到了。老人坚持了8天,但病情并未进一步恶化。他靠着自己活下去的决心,靠着自己能够克服困难的信念。 “当心理咨询在这里打开缺口时,寻求者看到,在没有特效药物的情况下,除了基本的治疗方法外,患者强烈的求生欲望才是最大的资源。”于雷说,看到希望后,杨力也开始明白武汉封城对于阻断疫情蔓延、对于全国的意义。 于蕾提醒杨丽,年迈的父亲虽然信仰坚定,但也需要她的精神支持和鼓励。 求救第三天,杨丽也开始出现低烧,体温为37.7℃。当玉蕾回电话问她感觉怎么样时,杨丽坚定地说:“我现在一点也不害怕了,我今天早点回家好好休息,如果体温还降不下来的话。” ,即便如此,我还是会进行血液检查和胸部 CT 扫描。”如果我真的被感染了,我也不怕。我从父亲那里找到了战胜病毒的方法,相信我能通过这次考验。” 特殊时期,“面对面”咨询不可能实现。
钟建明告诉记者,咨询方式从上到下依次是“面谈-视频语音-电话/语音-文字”。如果不进行采访,就无法收集很多非语言信息。一般热线电话会持续20-30分钟,最长不会超过50分钟。即使当事人确实想咨询,也建议先冷静一段时间再联系。 中恒在咨询过程中的遗憾是,很难在30分钟内为大家提供深入的支持。 “感染者、家人以及心脏比较脆弱的人,仅仅靠一两次辅导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需要不断的随访、一步一步的努力,逐步安抚情绪,恢复健康心态, ”于蕾说道。 及时治愈创伤 小波目前仍处于心理恢复期,隔离期即将结束。她不再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但她时常回忆起去武汉时的情况,“1月20日我去了武汉,当时的情况应该更严重,但街上很少有人戴口罩。一开始,信息没有公开”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公众都没有意识到。” “我最难过的一天是科比去世的时候。凌晨4点左右我就醒了,看了看手机,以为自己在做梦,然后又睡了。”小波说:“事故发生得很突然,不知道下一次事故什么时候发生,你过来吧。” 心理咨询“介入”时也会出现头痛、恶心等症状。 “辅导员很容易过度介入并陷入无力感。”于蕾说,“你要时刻回归自己,认识自己,分清哪些情绪是你自己的,哪些是客户的,哪些是你自己的同理心。” 有时候你无能为力。他们无法提供每个人最需要的病床、口罩和物资。 一些“卷入”的咨询师退出了心理咨询战。在于蕾看来,危机干预心理咨询考验的是咨询师的个人成长和技能。 “危机干预咨询是一场考验,所有参与的咨询师都在检验自己是否通过了考验。” 朱琳团队成立了督导组,专门负责重大案件和辅导员问题。钟建明负责督导工作。用他的话说,就是“前线作战,后院防火”。 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钟建明表示,目前我们联系到的求助者只是在疫情期间意识到自己有需要的朋友,他们只是整个受疫情影响人群中的“冰山一角”。 朱琳认为,疫情结束后,公众普遍的焦虑还将持续三个月左右。身体上的创伤很容易恢复,而心理上的创伤则需要随着环境和心态的改变而慢慢修复。危机创伤可以通过干预来治愈,但这需要足够的时间、适当的方法和合适的咨询师。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和生活经历不同,治愈所需的时间也会不同。 疫情期间,经历过无法就医或亲人病逝的群体可能受到的创伤更大。于雷提醒,这些群体的创伤需要后续积极的心理疏导和干预,政府和个人都应引起足够重视。 “这也和个人的性格特点有关,有的人可能会背负一辈子,有的人会因为生活中的意外而受苦。如果事件引发创伤,还是需要回去心理咨询修复它。” “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灾难过后,更多的人需要心理创伤的干预和修复,心理咨询工作任重而道远。”朱琳说。 新京报记者 王军 陈思主编、刘越校对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