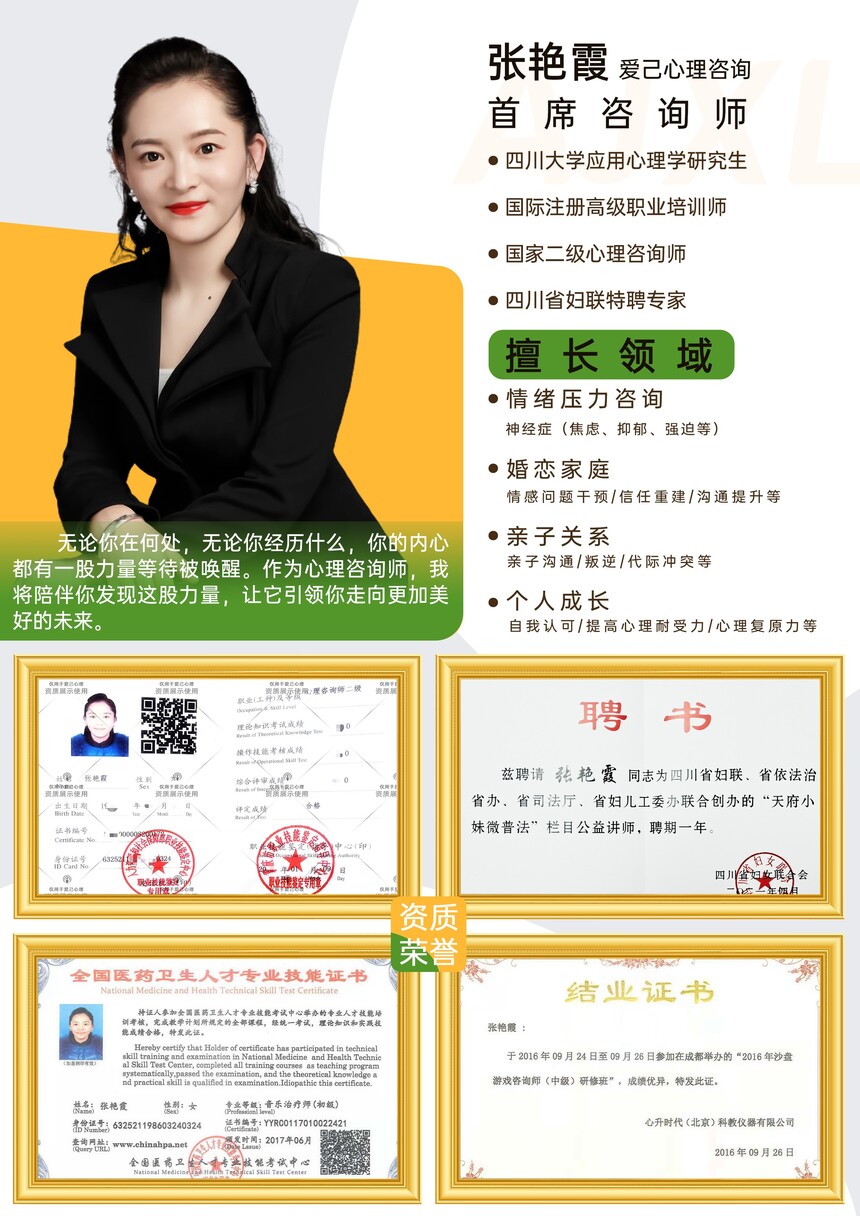|
儿童心理咨询|高校心理干预系统:从帮助到监视,学生心理健康的双刃剑时间:2024-12-05 14:05 近日,一篇题为《为何高校的“心理干预”体系越来越像“心理监视”体系?》的文章再次引发公众对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热议。 文章提到: 高校心理健康干预体系越来越完善,这是一件好事。但在一些大学生眼中,这个原本是为了“帮助”的系统,现在越来越像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 这双“眼睛”覆盖了“学校-部门-班级-宿舍/个人”四层“预警系统”。从学年初的第一次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开始,似乎就在关注每一个有“异常状况”的学生,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和挫折。当达到一定阈值时,一些大学甚至会向学生发出警报:“你心情不好,是否应该考虑请假?” 学校停课后,心理干预系统“眼睛”的存在逐渐被学生感知—— 有人发现,开学时进行的心理健康筛查量表让自己成为辅导员眼中的“重点观察对象”;有些人患有精神疾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称为父母”;有些人一时冲动,凡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自杀倾向”的人,都会被学校保卫处询问,“要么休学,要么陪你学习”…… 缺乏安全感在学生群体中蔓延。甚至有学生问:这个学校是需要解决心理问题,还是需要解决有心理问题的人? 2020年9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大学体检筛查抑郁如何保护个人隐私?》 “文章中描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某大学学生张戈在接受心理健康测试第二周,就被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传唤”到心理咨询室。同学们因此嘲笑他,怀疑他是因为精神失常而被叫去“喝茶”。 这让张哥感觉很尴尬。他确实因为青春期的灰暗和家庭背景,多年来积累了负面情绪。然而他不知道如何与外界沟通,只会越来越怀疑自己真的不正常。 另一位大学生张凡友的遭遇则更令人震惊! “有一次我好几天没有吃饭,负责心理咨询的老师对我说,如果你吃得不够,你怎么还有力气继续悲伤呢?”
张凡友觉得老师说的好笑,就去吃饭了。 但让张凡友生气的是,当她出于信任走进学校心理咨询室时,老师在签了保密协议后仍然向学院领导讲述了她的病情和经历。 “就像被人捅了一刀,当信任崩溃的时候,整个人就处于毁灭状态,那种对人性的绝望是没有人能理解的。”张凡友说。 张凡友2019年11月被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建议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 医生曾经告诉她:“没什么大不了的,吃药就可以了。” 但当学校从辅导员那里得知她的病情后,开始多次联系她的父母,要求将她送往医院。 为此,她与学校领导发生了一些言语冲突。 “也许在学校看来,患有抑郁的学生会自杀,所以他们必须停课住院并与其他学生隔离。” 张凡友永远记得,2020年5月,她在学校门口出示健康码后,就被送往当地精神卫生中心。 她被诊断出患有复发性抑郁症,并伴有严重的精神病症状,她的母亲和她一起住进了医院。 张凡友不被允许返回学校。毕业后,室友们帮忙收拾宿舍里的东西。 张凡友说,同校的一位高年级女生也向她吐露了类似??的经历。辅导员让她每天停课,并让父母带她去医院。 2020年11月7日,《中国大学要筛查抑郁,学生却怕暴露被劝退》一文报道了一名大学生的同样经历。
小树正在北方的一所名牌大学读书。从大二开始,他就一直受到抑郁的困扰。那年夏天,他去医院检查,被诊断出患有中度抑郁和轻度焦虑。 吃了一个暑假的药,感觉好多了,就停药了。 但进入大三后,沉重的学业压力让一切又回来了。 在患者群交流时,一名心理学研究生建议小舒去学校心理咨询室。 他们以为名校的心理咨询室应该更专业、更体面,但万万没想到,竟然这么不专业。 学校安静的心理咨询室里,刚刚升入大三的小舒不知不觉地暴露了抑郁。 “我的情况很糟糕,很痛苦。学业压力很大,要和那么多优秀、勤奋、爱思辨的同学竞争。有时我会想到死亡。”她说。 “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任何躯体症状,睡觉也没什么问题。” “太危险了。”老师听了这话,就这么说了,正准备给小舒的辅导员打电话,让她提供父母的电话号码。 小树一听,又急又生气,真的很生气,信任感一下子就消失了。 小舒在学校心理教室咨询后被拘留,心理老师要求家长将她接回。 小淑大闹了一场,直到学院党委书记来了,把她带回了办公室。 秘书安慰她,说学校的心理咨询很不专业。这位心理学老师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她就会去看心理医生,或者寻求外界的心理咨询。一切都平静下来了。 那次遭遇后,小树认为“系统不可信”。 因此,当中国政府宣布将进行抑郁筛查时,她的本能反应就是恐惧和不适。 “这真是害死抑郁患者!如果你觉得我们死得慢,就推我们一把!”她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篇文章。 在中国,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被学校视为“安全隐患”已是不为人知的秘密。一旦发现学生患有精神疾病,大多数学生都会被要求停课。出于安全和责任的考虑,学校会主动泄露学生的隐私,告诉别人他们的“秘密”。 网络上有关大学心理咨询(机构)“泄密”的投诉也屡见不鲜。 然而,人们在关注高校心理咨询机构“东场化”,甚至指责高校心理咨询不专业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 2015年8月,大学生苏某在宿舍内自杀。警方勘察现场后,发现苏在笔记本电脑桌面上留下了遗书,记录了他的个人密码和英文(谁也不能责怪,希望尽快),并认定苏有服用苯巴比妥。因钠中毒而死亡。 事发后,苏家人声称XX大学对苏自杀有过错。他们认为,XX大学在新生心理健康调查中明确知道苏患有中度精神疾病,也知道他拥有自杀药物和毒品。尽管他自杀了,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阻止苏,也没有将上述心理问题和行为告知学生家属,从而导致了苏死亡的悲剧。 XX大学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据此,苏家人向法院请求:判令XX大学赔偿苏家人死亡抚恤金及丧葬费0.2元; 2、责令XX大学向苏某家属支付精神损害抚慰费2元; 3、责令××大学向苏家属支付慰问费人民币2元。 2、支付苏家属办理苏葬的费用。 4、责令××大学承认在处理苏自杀的过程中存在严重不当行为,并向苏家属书面道歉; 5、提起诉讼 费用由XX大学承担。 作为被告,XX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注册督导员李某在庭审中被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说明其在苏自杀事件中履行职责的情况。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学生因心理问题发生自残或自残行为时,高校心理咨询(机构)是首要问责对象。 这就导致,高校心理咨询(机构)面对有心理问题(疾病)的学生,尤其是有自杀、自伤、风险的学生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如何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帮助。同学们,却如何保护自己。
否则,一旦学生自伤或自伤的责任落到高校心理咨询(机构)身上,将直接影响其成绩和升职。 在大多数高校心理咨询(机构)的工作中,恪守职业道德和履行工作职责已经是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 尤其是在涉及学生自残、自杀的危机案件中,严重的“责任焦虑”使得高校心理咨询(机构)更倾向于选择伦理突破来规避风险。 此前,搜狐旗下吉州工作室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心理咨询的道德困境》的文章,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揭示了大学心理咨询在工作中面临的诸多困境。 一方面,高校心理咨询(机构)被指不够专业,频频泄密“监视”学生;另一方面,当学生因心理问题发生自残或自杀行为时,被家人指控未尽告知义务,甚至将被告告上法庭。 很多时候,这种职业道德与工作职责的矛盾要求,使得大学心理咨询(机构)就像生活在夹缝中的老鼠,里里外外都不再是人了。 多篇文章分析,高校心理咨询机构“东场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行政化和“问责”导向的管理机制。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已将心理咨询机构纳入行政部门进行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心理咨询的工作需要接受上级行政部门的指导。教育管理者和职业帮手的双重身份,使得高校心理咨询在工作中总是捉襟见肘,甚至不伦不类。 在高校行政部门眼中,心理咨询仅被视为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工具,是高校心理咨询行政部门(机构)的附庸。 面对需要心理援助的学生,行政部门的强行介入,使得高校心理咨询的专业作用难以发挥,甚至不得不违背职业道德去满足上级行政部门的无理要求。 一位大学心理咨询曾向我们抱怨: 全职从事大学心理咨询十年,咨询量少得可怜。省教育管理部门领导公开表示,专任教师参加培训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参加这么多的培训,更不用说是哪个省的了。他们还明确表示,向心理咨询中心专职老师咨询并不是主营业务。所以,你看,打零工是不可避免的。缺乏系统监管,缺乏专业培训,行政事务较多。每次学生预约咨询,与行政工作发生冲突时,必须要求与学生再次预约。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将高校心理咨询机构“东长化”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个别高校心理咨询显然是不客观的。不应该把责任归咎于大学心理咨询。 高校心理咨询也会因专业工作的“东场化”而产生激烈的内心矛盾和冲突。 事实上,心理咨询越认同所学理论中隐含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西方价值观,他们就越讨厌在体制内工作。 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心理咨询对“自我和自由”的强调,会导致心理咨询下意识地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与东方文化背景中“集体主义”和“系统工作”的价值观不符。 。产生矛盾和冲突。 某种程度上,体制内心理咨询所遭受的职业痛苦和职业认同危机,实际上是心理咨询“文化适应性”问题的两个侧面。 当心理咨询这一西方文化的产物传播到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时,不可避免地会经历适应阵痛。 作为身体内部的个体,内部心理咨询对此自然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需要认识到的是,在文化矛盾和冲突中,任何个人都不应该成为受到严厉批评的人。 成长组: 指导小组: 研究组: 关注拉康心理学公众号,查看最新行业新闻和精彩文章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