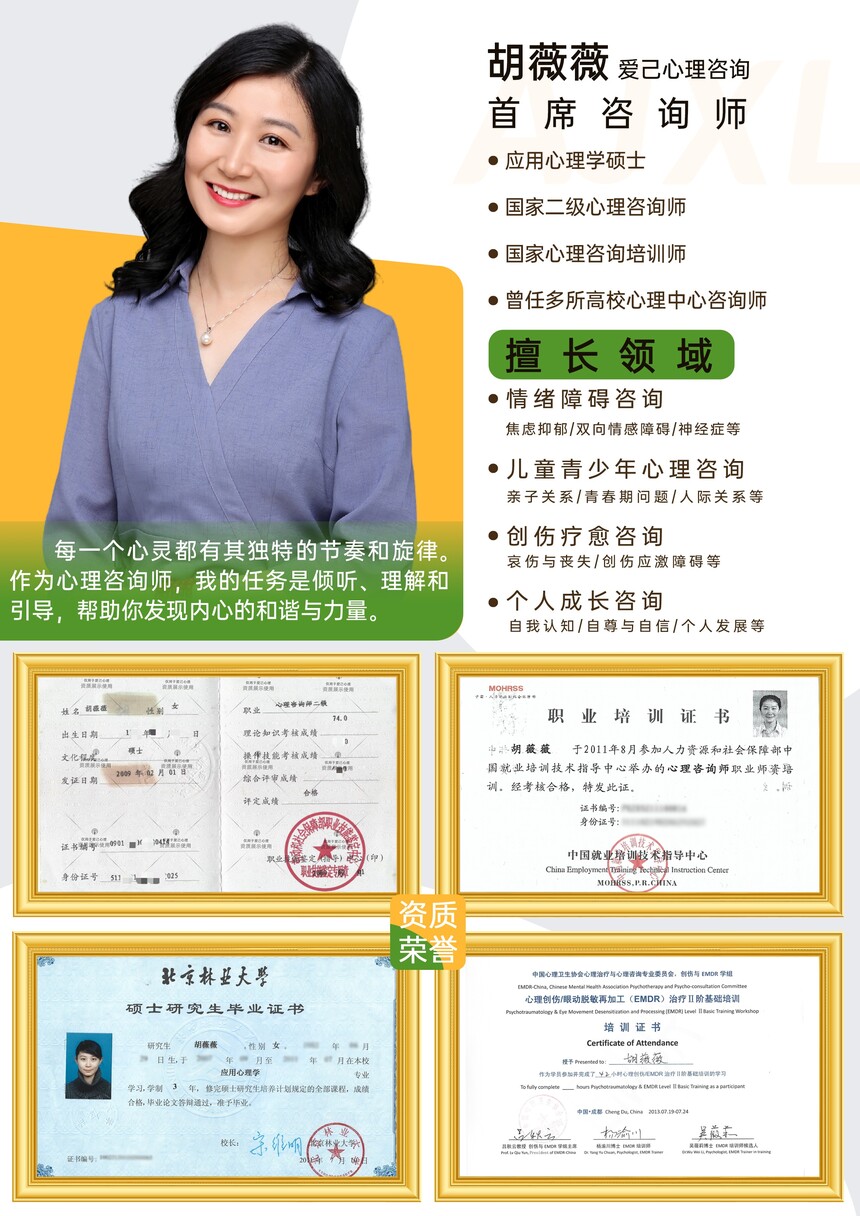|
成都心理医生|成都精神卫生专家赴武汉:患者和医护人员都需要情绪干预调整时间:2024-11-05 14:08 成都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刘田表示,希望对医护人员的心理关注和服务更加细致、持续。由于我们还处于抗压阶段,医务人员的心理问题往往被忙碌的工作和当前疫情的严重性所掩盖。医护人员往往还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成功抗击疫情,除了物质装备外,还需要心理支持。 精神科医生也是全国各地驰援武汉医疗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要支持病人,还要支持他们的战友——医护人员。 01 患者和医护人员都需要情绪干预和调整 2月13日,成都市派出本市第一支精神卫生专家组奔赴武汉。这支专家团队来自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成都市精神卫生中心)。此后,医院又派出第二批精神卫生专家组赶赴武汉。 今天,医院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刘芳博士等六位心理专家奔赴武汉一线;主治医师耿婷、周游;而心理治疗师刘天、唐克、聂晓静集体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独家专访。 NBD:目前,各地向武汉派遣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数量日益增多。您认为这样做的原因和考虑是什么? 刘芳:心理因素在COVID-19的治疗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病人的角度,我们经常从视频和抖音上看到,在方舱医院,很多病人都组织在一起做健身操,互相娱乐。气氛感觉很轻松,完全不像是在医院里的感觉。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心理因素对患者康复的积极作用。 从医护人员的角度来看,自从第一批医护人员赶赴武汉驰援以来,很多人的工作时间都变长了。他们长时间穿着隔离服上班。尤其是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每天都需要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面对诸多压力事件,一些医务人员会出现过度疲劳、紧张、焦虑、失眠、抑郁、自责甚至疲惫不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对医护人员进行情绪干预和调整。 为了工作方便,刘芳让同事把长发剪短了。 唐克:随着COVID-19疫情到了关键阶段,一方面,医护人员的身体和心理状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疲惫,这些临床医生和护士有心理援助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收治患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和好转,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的部分患者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情绪问题和睡眠问题。患者人群也是我们心理援助的目标群体。 NBD:您与 COVID-19 患者有过互动吗?如果您和他们有过交流,您接触过的患者目前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为患者提供心理咨询?
刘芳:我曾经给一位重病患者通过电话进行心理治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整个治疗过程中,虽然患者戴着两层口罩,说话有些困难,但说话的欲望依然很强烈。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过程中,病人是在她的爱人生病时开始的。在此过程中,她描述了自己如何照顾爱人,有时甚至忘记采取隔离措施。尽管她竭尽全力照顾爱人,但爱人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情况还在恶化。 那段时间看病的人很多,最后都是她老公在家吃药。看着丈夫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她心疼不已,想做更多的事情。每每想到这里,她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没能挽救爱人的生命。 整个谈话过程中,她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把事情解释清楚。她一度哽咽,但她还是想和我们沟通,表达她对离开爱人的不舍和遗憾。 后来,这些不舍逐渐减少,她也相对更加接受了爱人的去世。随后,她开始讲述儿子、孙子等亲人的情况,以及如何开始面对未来的生活。 整个采访过程中,患者表现出更多的悲伤。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尽量让患者通过倾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压抑自己,偷偷哭泣。她告诉我们的过程就是一个情感释放的过程。 02 避免过度英雄化医务人员 NBD:您在为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时,您发现医护人员面临哪些具体困难?他们普遍的积极和消极情绪是什么?另外,从一些细节来看,不同科室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阈值是否存在差异?舆论的走向对他们有影响吗? 刘田:具体困难在于,一线医护人员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医疗救援任务,而且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每天都会接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面临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病人的死亡、医护人员的感染、与他人缺乏沟通、睡眠不足,都导致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骤然增大。 他们较常见的负面情绪包括焦虑、紧张、烦躁、悲伤、无助、恐惧、没有安全感等。此外,睡眠问题也很常见。 但医护人员也表现出了更多的韧性和毅力。他们往往显得比普通人更坚强,更不容易崩溃。他们经常积极地调整自己,采用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 心理治疗师刘天(右)与医护人员交流
不同科室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阈值确实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医护人员面对的重症患??者越多,他们内心的压力就会越大。他们往往面临更多的生死,承担更多的职业暴露风险,因而遭受更多的内心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心理压力阈值会更高——他们更善于自我压抑或释放情绪,以保证自己不崩溃。 舆论对他们的赞扬确实有积极的鼓励作用,但也要注意避免过度“英雄化”医务人员。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也是有负面情绪、恐惧、焦虑、有时感到无力的普通人。只有当公众和舆论明白他们也是普通人的时候,才能更好地接受自己的这一部分。 NBD:你们如何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咨询? 刘田:医务人员个体心理咨询方法基本可以遵循以下步骤:建立关系——宣泄情绪——共同挖掘自己可用的心理资源——结束咨询。 我最近接触到了一位医护人员。起初他拒绝和我说话,并认为一切都很好。尽管他有睡眠问题和身体问题,但他仍然带病上阵。 我同情他可能不愿意让自己感到无能为力,赞扬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在第一线,并通过这种支持技术与他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他有更多的空间,被允许谈论他所坚持的东西——那就是深深的无助和愧疚,失去生命的痛苦和他的无助(宣泄情绪);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和探索一些他可以用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资源,比如和家人朋友聊天,自己做一些放松的运动等等(挖掘自己的心理资源);最后,我再次肯定他的努力和坚持,以及更多的鼓励,结束了咨询。 随访中我们了解到,医生真的开始和同事倾诉自己的感受,并开始做运动。心理疏导发挥了一定作用。 NBD:根据您的工作实际,您认为需要在哪些方面、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关爱? 刘田:无论是出台保障医护人员安全、保证他们充分休息的政策措施,还是加大力度提高他们的待遇、照顾好他们的家人、消除后顾之忧,这些努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角色。我们也注意到,精神卫生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大批精神卫生工作者开始落户武汉。 我们希望对医务人员的心理关注和服务更加细致、持续。由于我们还处于抗压阶段,医务人员的心理问题往往被繁忙的工作和当前疫情的严重性所掩盖。医护人员往往还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我们必须警惕疫情结束、放松后医务人员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现象。届时,部分医护人员可能会出现噩梦、性格改变、情感游离、麻木、失眠、回避引发创伤记忆的事情、易怒、过度警惕等症状。 因此,我们对医务人员心理的关注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心理服务,确保他们能够真正克服疫情对身心的影响。 03 关注疫情后被忽视的心理问题
NBD:您认为疫情过后,可能会出现哪些在压力下被暂时忽视和掩盖的心理问题?您对此有何建议? 刘田:术后患者和医护人员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此前的研究表明,在对受地震等灾害影响的群体的调查中,3个月内和9个月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率分别为18.8%和24.2%。 在这次疫情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直接失去了亲人,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人目睹了大量的生死,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对此,首先要开展心理健康宣传,让患者和医护人员正确认识疫情结束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消除因概念模糊而产生的焦虑、抑郁;其次,要帮助当事人及其家属学习相关知识,让家属了解当事人的痛苦和困境,让家属多与当事人沟通,协助当事人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合理宣泄痛苦情绪,让当事人接受自己的不幸和无力;第三,必要时寻求专业心理帮助。 耿婷:疫情对人们来说是一个极端的压力事件。人们的心理会(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运用各种策略来应对压力状态的突然变化:比如本能反应(战斗——)在昏迷中,人变得极度麻木,隐藏与灾难相关的负面情绪体验;比如,在紧张的状态下,人会变得极度麻木,隐藏与灾难相关的负面情绪体验;比如,本能的反应(战斗——),使人变得极度麻木,隐藏与灾难相关的负面情感体验。又如否认或隔离疫情对自己内心的重大刺激;另一个例子是压抑和隐藏内心的恐惧和负面经历等等。 这一系列的方法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一种错觉。有些人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特别稳定、冷静,但一段时间后很可能会产生心理问题,甚至出现消极的想法。因此,在疫情期间开展心理评估,筛选重点人群进行专项干预,并在疫情结束后继续进行心理随访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要加大对心理问题识别的科普力度,提高广大群众识别亲友潜在问题的能力,并与专业筛查相结合,实现有效预防和预防。 04 疫情尚未结束,不能放松 NBD:目前各地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您对此有何看法?疫情结束后,您对大家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建议? 周友:从疫情数据来看,确诊病例数有所下降,很多城市甚至连续多日实现零病例。大家都觉得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如果他们感到放松,他们的行为和表现可能会变得松懈。对于试图聚集的行为,佩戴口罩和手部卫生程序并未严格执行。 我向大家呼吁:疫情已得到控制,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就像赛跑一样,看到终点并不代表胜利。这个时候你不能放慢脚步。只有真正跨过终点,你才能相对放松。 聂小晶: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了生命威胁。未来我们也可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想想有哪些可以调整和改变的地方:一是在减少与外界直接接触的同时,我们该如何与自己相处?和对话,发现其中的乐趣,自己的价值观能不能部分调整,找到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东西?其次,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相互联系方式。疫情结束后,我们能否丰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第三,手卫生、戴口罩、保持适当距离是有益健康、有价值的新行为。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 |